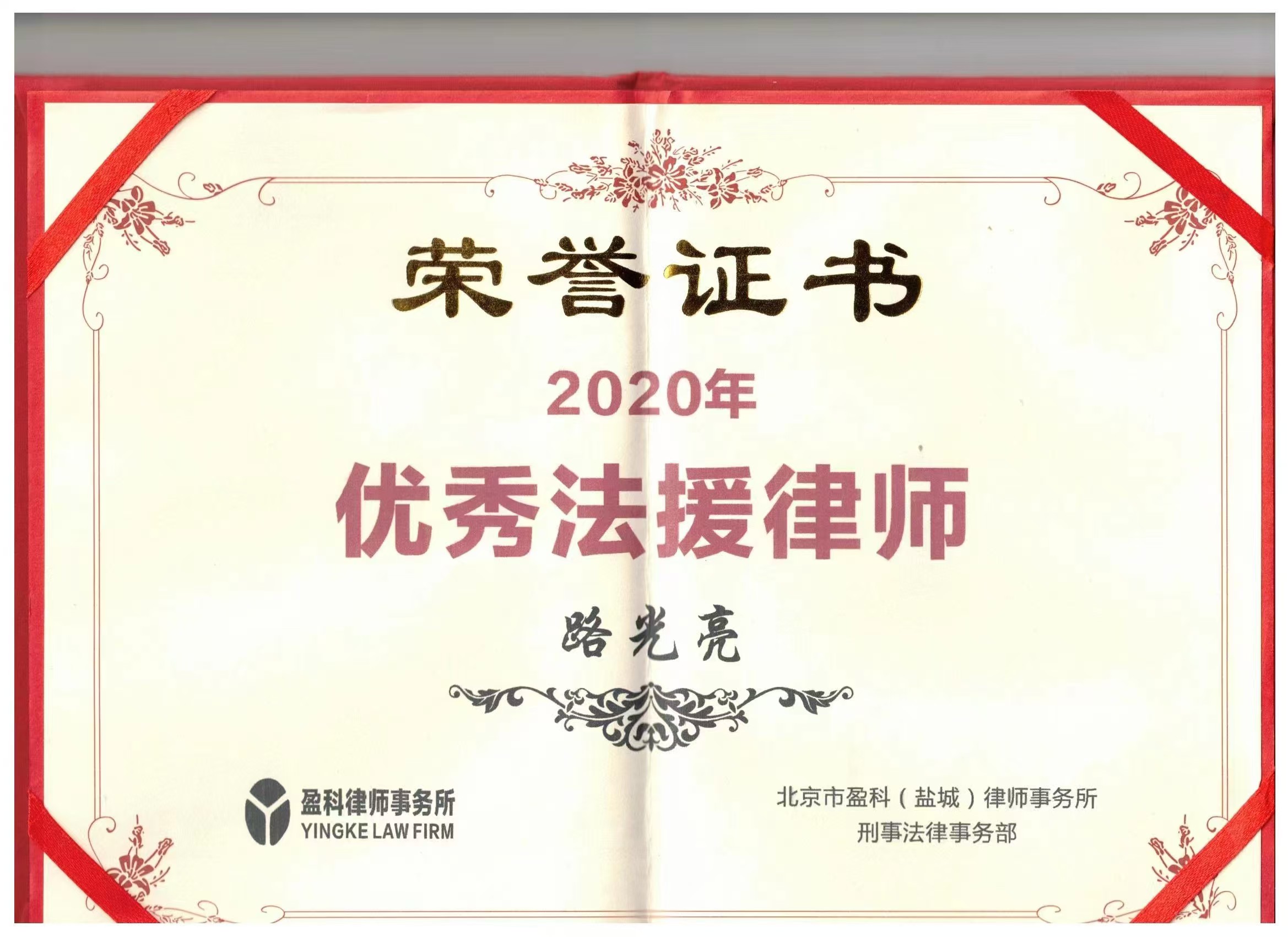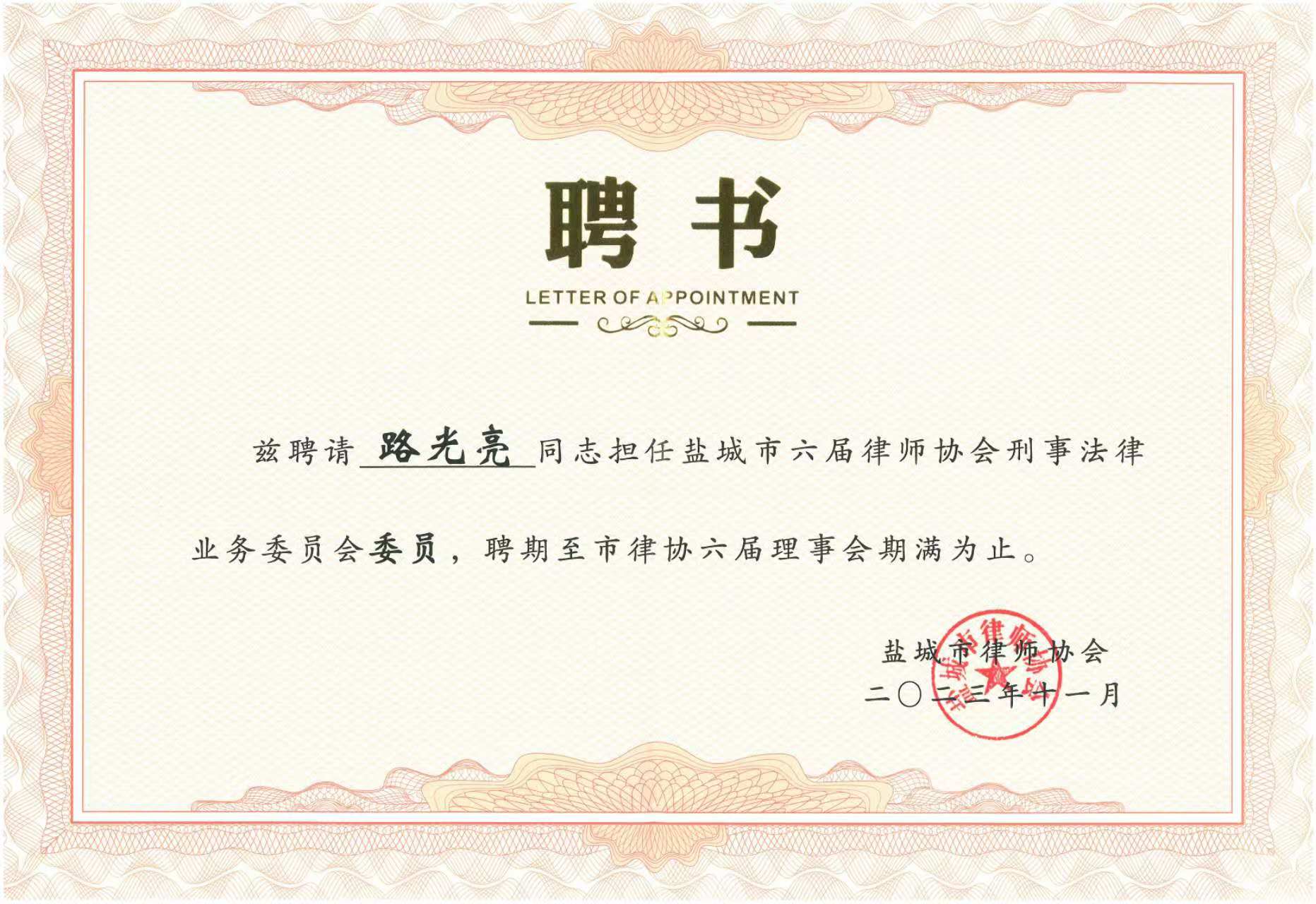傍晚时分,电脑屏幕的光映在小陈的脸上。26岁的他刚从技术学校毕业,在一家小型软件外包公司做程序员。那天,他收到一份朋友转来的“兼职链接”,内容写得很诱人:只需要在后台帮助客户搭建数据接口,就能轻松获得丰厚报酬。小陈没有多想,凭借自己的技术,很快完成了对方的需求。可他并不知道,这一次操作,却让他卷入了一起严重的网络犯罪案件。
几天后,警方上门,小陈被以涉嫌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”刑事拘留。看守所的第一次会见中,他的眼神充满迷茫,不停重复一句话:“我只是写了几行代码,怎么就成了犯罪?”
案件的另一面
王律师作为辩护人,接手案件后调阅卷宗,很快发现问题的关键。小陈确实没有直接参与诈骗行为,但他提供的程序接口,恰恰是电信诈骗团伙批量收集用户信息、转移资金的技术支撑。在法律上,这种“帮助行为”并不会因为“没有主观诈骗意图”就自动免责。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明确规定: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,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、服务器托管、网络存储、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的,属于犯罪。
然而,“明知”与否,往往是此类案件的最大争议点。小陈坚称自己只是接到普通的外包请求,并不清楚客户的真实用途。但办案机关认为,短期内高额报酬、规避实名信息等明显异常,足以让他意识到其中的问题。
辩护的艰难抉择
在会见过程中,王律师没有直接给予轻率的承诺。他很清楚,在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”活动案件中,如何认定主观故意,是辩护的焦点。要想为小陈争取更轻的处理,必须找到能够支撑“非明知”的证据链。
于是,律师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:
合同与沟通记录
律师要求小陈家属尽快调取与客户的聊天记录、任务合同和转账凭证。如果沟通内容中客户刻意隐瞒真实用途,且小陈并无主动询问的动机,那么“明知”的认定就会削弱。
程序功能的专业分析
王律师邀请了独立的计算机专家,对小陈编写的接口进行技术鉴定,证明该程序本身属于通用工具,具有合理的商业使用场景,而不是专为诈骗设计的“定制工具”。
涉案金额与角色定位
辩护意见书中强调,小陈只收取了固定的技术费用,与诈骗团伙的获利金额无直接关联,不存在“共谋分赃”的情形。其角色更接近“外部工具提供者”,属于从犯或情节较轻的帮助行为。
庭审的对峙
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,检察机关依然坚持指控。庭审当天,控辩双方围绕“明知”进行了激烈辩论。
公诉人指出:小陈在明知对方提供的虚假信息、避开合同条款约束的情况下,依然继续操作,说明其具有应知甚至明知的心理状态。
而王律师则据理力争:“刑法评价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,而不是推测。单纯因为高额报酬就断定被告人具有明知,显然欠缺充分性。我们有完整的技术鉴定意见和交易凭证,可以证明小陈的行为具有常见商业逻辑。”
判决与余波
经过两轮辩论,法院最终采纳了部分辩护意见。小陈被认定为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”从犯,处以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,缓刑二年,并处罚金。这一结果让小陈和家属既感到沉重,也算稍稍松了一口气。
走出法院的那天,小陈告诉王律师:“我以后再也不会随便接陌生的技术活了,哪怕再高的价钱。”他的声音里带着惶恐,也带着对未来的清醒。
透过案件的警示
在这个故事里,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年轻程序员的遭遇,更是网络时代中普遍存在的法律风险。许多从业者习惯于以“技术中立”为借口,忽略了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刑事责任。可法律的逻辑并不是技术能否被滥用,而是你在接受任务时是否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。
网络犯罪的隐蔽性和跨境性,使得侦查与认定都格外复杂。一个“无意间的点击”,一个“不经意的外包任务”,都可能成为卷入案件的导火索。而对律师而言,如何在“主观明知”的模糊地带中寻找突破口,既考验专业功底,也考验责任感。